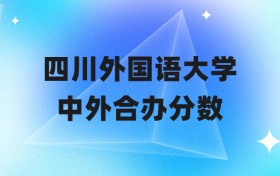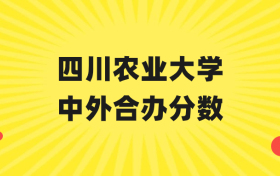近日,顶尖学府复旦大学宣布文科招生比例从原来的30%-40%骤降至20%。
全网文科生集体破防——有人翻出张雪峰那句“文科都是服务业”的暴论,有人自嘲“选文科等于49年入国军”......
1977年冬天,关闭十年的高考考场重新开放,570万考生挤在破旧的教室里争夺27万个名额。那场考试中,文科状元的名字被印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,哲学、历史学成为最炙手可热的专业。
谁也不会想到,46年后,中国顶尖学府会举起改革的手术刀,将文科招生拦腰斩断。

翻开世界教育史,每一次文科的兴衰都暗合文明迭代的密码。
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,牛津剑桥掀起“古典学大辩论”,最终将希腊语拉丁语课程压缩30%,为工程学腾出空间;20世纪80年代,美国高校砍掉40%人文学科,转身拥抱计算机浪潮。
如今复旦的20%文科招生红线,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又一道刻度。
尽管招生比例下降,但复旦校长金力一直强调“文科并非不重要”,这背后藏着残酷的进化逻辑:
1950年代苏联援建时期,中国高校工科占比飙升至70%;
2000年代全球化浪潮中,经管法学成为文科新贵;
2024年人工智能奇点逼近,数字人文站上潮头。
这让人想起明治维新时的日本:东京大学一面裁撤汉学课程,一面高薪聘请德国哲学教授。文明转型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,而是要在断裂处重建秩序。

在复旦宣布改革的同一天,硅谷传来消息:斯坦福“科技伦理中心”获得马斯克1.2亿美元捐赠,前提是必须招收30%哲学系学生。
这场横跨太平洋的文科攻防战,暴露了全球精英的共识:
1. 美国的困局
西弗吉尼亚大学裁撤外语系时,校长坦言:“我们培养出太多只会解构《哈姆雷特》的毕业生,却没人能制定AI监管法案。”
这种错位导致美国科技巨头不得不从印度进口“懂梵语的程序员”,从德国引进“熟悉康德哲学的算法工程师”。
2. 中国的破局
复旦新建的6个交叉学院,藏着顶层设计的深意:
集成电路学院必须修读《科技政策史》。
智能机器人专业嵌入《资本论》研讨课。
生物医学工程与医疗社会学捆绑培养。
这让我想起钱学森之问的另一种解答:当年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中,王大珩是物理学家兼诗人,邓稼先能背诵整部《史记》。真正的创新,从来诞生在文理交汇的裂缝中。

在深圳科技园区,一场特殊的招聘正在上演:
华为开出百万年薪寻找“会编程的哲学家”;腾讯AI实验室争夺“懂量子力学的历史系博士”;
字节跳动组建“科技伦理委员会”,成员清一色人文背景。
这些场景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:当流水线式文科教育撞上AI革命,传统人文学科正在经历“适合生存,不适者淘汰”的过程。
复旦的“20%精英化”路线,实则是转向更高层次的定位:
裁撤重复性人文学科,聚焦数字人文、科技伦理等战略领域;将文学批判思维植入工科课堂,让人文基因在代码中延续;
五大书院制暗合宋代书院传统,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构“师承体系” 。
这种转型早有预兆:2023年教育部新增审批专业中,“未来哲学”“智能法学”等交叉学科占比达68%,而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撤销数量创十年新高。

那些喊着“文科已死”的人或许不知道:敦煌研究院用AI修复壁画时,最紧缺的是精通佛教艺术史的算法工程师;宁德时代研发钠离子电池过程中,社会学团队解决了跨文化管理难题; 甚至OpenAI训练GPT-5时,专门聘请了儒家学者构建伦理框架。
真正的危机不在文科本身,而在文科教育能否跳出“之乎者也”的老套子。就像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催生了宗教改革,今天的人工智能也在倒逼人文精神的重构。
别被复旦的招生比例吓到,看着是砍文科,实则是逼着文科生“上科技树”。
就像苹果淘汰了诺基亚,但没淘汰通信需求——变的不是需求,而是工具。历史从不淘汰文科,只淘汰固步自封的文科。